“希望的原理”策展文章六:被遗弃的未来
中间美术馆新展览“希望的原理”已于2021年10月16日开幕,我们将在之后的推送中,发布来自总策划及策展团队成员的六篇策展文章,向观众呈现展览筹备过程中,团队成员对当下所处环境的思考,以及各自切入未来讨论的角度。虽然驱动我们反思现有未来想像所施加的桎梏的现象不尽相同,但我们同样朝着一个方向努力着——在沉重的现实之中寻找超越的缝隙,主动地创造而非被动地接受允诺的未来。策展人印帅通过探讨“被遗弃的未来”,以求在进步的现代文化逻辑下,从未来的视野将目光聚焦于当下是如何被塑造的,重拾未来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提出艺术家将某个未来世界的遥远过去呈现在我们面前,在空间上构造了一种陌生化的想象,质疑了“唯一”存在的未来。

被遗弃的未来
印帅
科技是答案,但问题是什么?—— 塞德里克·普莱斯
1909年2月20日,“未来主义”宣言发表;1913年,福特工厂生产线投入运营,几年之间的这两件事让未来与乌托邦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生产、意识形态以及艺术的核心,让“未来”的世纪充满希望。对未来的希望伴随着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经济对物质(产品)与非物质(知识)的不断扩张与增强,在20世纪达到了顶峰,形成了社会唯一可预计的期望,成为一种基于“进步”概念的真正信仰,也对经济增长现实的意识形态进行着预测与转译;同时,在进步的现代文化逻辑与线性的时间中形成的观念,削弱了对未来的想象力。柏林墙的倒塌,彻底使其被资本主义所独享,变成了一种带有伪装性的预感主义,沿着短期的线性历史发展不断加速,形成了一种更加单一的、符合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并且更具有生产力的趋向。
这一趋向遗弃了未来关于自身想象的多样性:在通信之外,随着金融交易中算法时间和非人类时间变得越来越相互纠缠、复杂,人类开始控制环境、控制时间、控制身体、控制希望,不断提高对所有内容的控制,防止一切背离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可能性的出现,利润、积累、竞争成为了社会利益技术具体化的标准指标。因此,当再度谈论未来的时候,人们很难再在希望之中寻得其踪;一并被遗弃的是蕴涵在另一未来叙事中的可能性:在单一世界所形成的知识生产与权力结构中,人们因此不再去思考如何创造,而开始思考如何控制,“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一旦认识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

“希望的原理”展览现场
艾瑞克·贝特伦,《被解释的世界》,2008 – 2011/2021,装置,尺寸可变
讨论被遗弃的未来,并非以否定未来作为其性质,而以不再简单地强调未来的图像与愿景为目的,以“未来政治学”为方法,从未来的视野将目光聚焦于当下是如何被塑造而成的。单一世界叙事和多重被压抑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是对殖民权力结构的瓦解;重访“被遗弃的未来”恰好可以重拾多样性与另一种可能性,将当下作为历史来理解,转入“幻想”空间之中,横向而非纵向地观看未来,与那些不同的性格、文化,不同的世界观和宇宙观的冲突相遇;重新发现,在二元对立逻辑外的另一些问题与可能:《被解释的世界》通过研究个体知识结构的语言图表,将“非专业知识”看作另一种知识形式;《YWY,仿生人》虚构了与玉米交谈的虚构仿生人,通过科幻场景质疑着技术控制下的线性未来;《Poyers!》则通过再现19世纪最大胆的金融骗局,将经济对未来远景的控制进行转译。艺术家连接了空间而非时间概念上的“未来”,将某个未来世界的遥远过去呈现在我们面前,构造了一种陌生化的想象,质疑了“唯一”存在的未来,同时提出了另一些想象。

“希望的原理”展览现场
佩德罗·内维斯·马尔库斯,《YWY, 仿生人》,2017,录像,7′
展览呈现了随着时间推移被边缘化、被压抑或者被遗忘的未来,尝试讨论它们出现的原因以及根植于内部批判的研究,成为实现撬动“未来”叙事的可能,其自身转变成为“颠覆未来”的场所,从未来的趋势中抽离,绘制多种场景,呈现多种可能性,重现那些既不是前瞻性的也不是乌托邦式的、疏离的陌生经验。

张哲熙,《波亚伊人!》,2021,视频(静帧),40′

印帅
印帅(1991)是一位中国策展人,工作生活于米兰与上海。2015至今担任米兰FM当代艺术中心艺术策展助理,米兰NABA视觉艺术与策展专业学术助理,2018年起留校任教。其发起的出版计划“AP Project”与德国Archive Books出版社合作,出版当代艺术思潮系列图书。其项目《珊瑚岛上的死光》入选2021年PSA青策计划,《幼年与历史》参加2019年OCAT研究型策展方案入围展,他作为策展团队成员参与北京中间美术馆展览《希望的原理》,2017、2018年他作为策展助理参与了银川双年展、安仁双年展、《四川故事-中国:戏剧与历史》、《白种猎人-非洲当代艺术展》、《未结盟的现代性》、《超越记录:意大利的70年代》等。其文章及译文曾发表于《Segno》《公共艺术》《L@ft》《Mousse》《画刊》《信睿日报》《艺术新闻》等专业艺术杂志。
编辑:马奕奕
微信排版:王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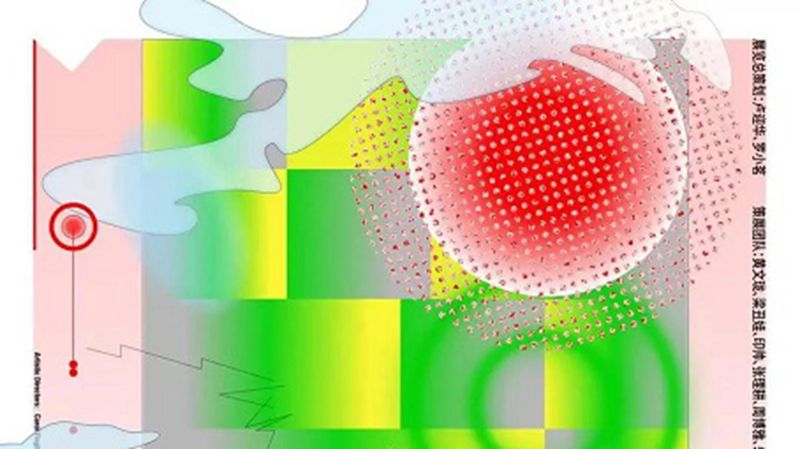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