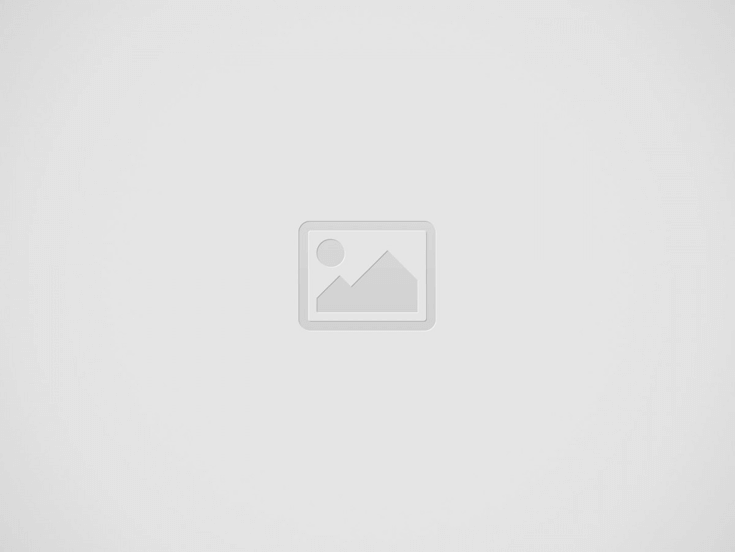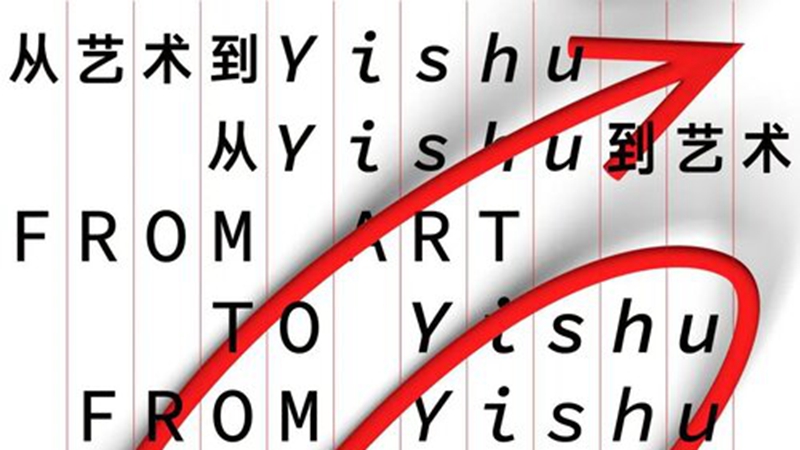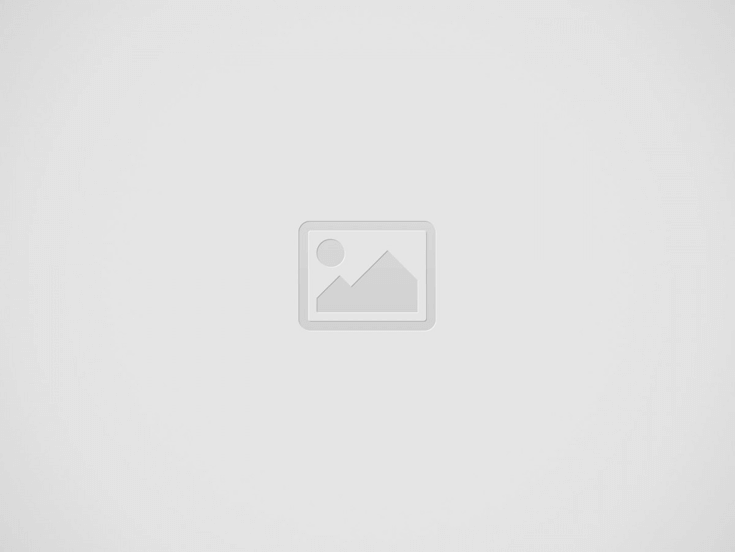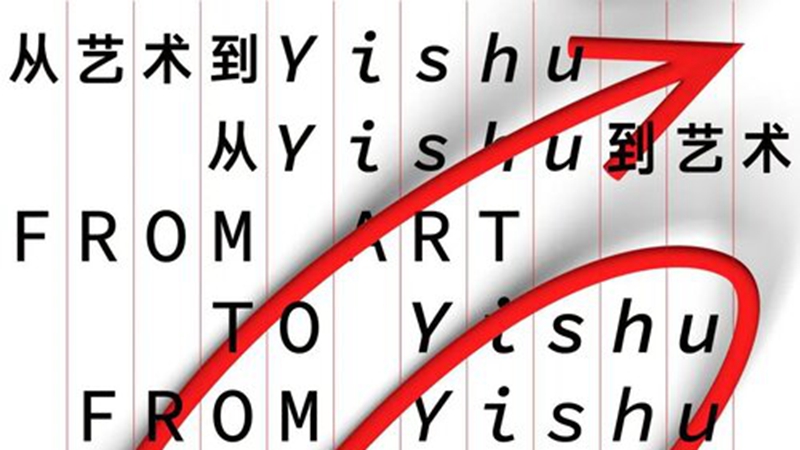1. 你和《Yishu》的故事是什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为《Yishu》写作的?
我从《Yishu》创刊以来就为它写作,是郑胜天老师邀请我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的。
2. 你在《Yishu》中发表过几篇文章?主要写作的内容是什么?
七篇左右吧。在《Yishu》初期,我写得比较频繁,很多是与我的研究兴趣有关的各类主题文章,而不是展览评论。
3. 你为什么会选择《Yishu》平台?你觉得《Yishu》杂志的特点是什么?它有哪些特质是不同于其他杂志的?
有几个原因:一是它是我的专业领域;其次它是一个独立的、非商业性杂志;还有就是它具有开放性,为年轻的研究者和边缘课题提供了发展、发挥空间。
4. 跟《Yishu》杂志编辑部合作沟通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畅通无阻而且专业。
5. 你的研究方向是什么?你最近在研究什么?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策划了几个展览。我的研究领域没有改变,我的兴趣仍然是当代艺术、艺术策略和文化政治的联系。
6. 2002年《Yishu》创刊号向当时的有影响力的艺术实践者提了一系列问题。借第100期出版之际,我们想把这些问题提给你:你怎样看待中国艺术文化现状?中国的艺术和文化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的艺术和文化对你来说是什么?“中国”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中国”这个词对我来说有多重含义,不同含义皆有所区别。
首先,中国是我丈夫的原籍国,这意味着我在中国有家人。其次,它是一个我众多好友生活的地方,是许多艺术家和艺术从业者生活的地方——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都与他们一起工作。
我年轻时在中国学习了近三年,从1985年到1987年。当时去中国就像去月球一样,它就像整个世界的一颗卫星:既现实又遥远,跟随西方也想要影响潮流,但尚不是世界的积极推动者。中国仍是社会主义阵营(Eastern bloc)的一部分,如此不同的地域。我有幸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最杰出的时刻——所谓的“85新潮”。当时我的经历以及与艺术家的接触使我决定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工作。我深深地被艺术家们强大的能量和意志所感动:他们一无所有,连工作室都没有,但他们能够改变环境,用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改变中国。
我相信,这种能量仍然存在。中国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从未失去过生命力。上世纪80年代,作为官方指导思想的乌托邦现代意识形态是文化领域的主要推动力。在这种乌托邦式的追求中,以七八十年代至20世纪末最为典型,中国加入了世界的发展浪潮。发展不仅被视为一种经济因素,还被看作个人和精神上的努力。人们追求的是更好,而不是更多。我不想说得很老套,但我认为,我们需要给这种能量一个机会,给各个领域的艺术家和创造者——无论是文化还是科学领域,一个参与社会转型的机会。政治不能也不应该解决我们当代世界面临的所有问题和挑战。我相信,个人是每一个持续变革的关键因素,而我们需要信任每一个个体,才能强化和实现变革。
7. 你认为目前艺术评论的现状如何?
就像其他所有东西一样,它需要更多的想象,更精准的文字。
8. 借用华思睿在第一百期向写作者进行的提问:“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当代艺术在艺术生产和运作机制方面有些什么发展/变化?”,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
有很多重大的变化。这个问题我曾在《Yishu》100期上详细回答过,我归结为以下:郑国谷曾对我说过,在他看来,政治口号是某种咒语,只要我们经常重复,就会变成现实。正是口号改变了现实,随之而来的是经济体制结构、价值体系以及艺术政策的改变。从70年代末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到2000年的“三个代表”、2005年的“和谐社会”,再到2008年奥运会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后文见置顶留言)(《Yishu》,第19卷,第5/6期(2020年):4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