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巨浪与余音”展七|“语言纯化”的两个音区(上)
在“巨浪与余音”展期间,我们定期按不同主题分享展览中的具体内容,为观众进行展览“导读”。借助展览中对具体作品、文献的描写,带领大家对1987年前后中国艺术的个案、现场及思潮进行“重访”,回溯1980年代中后期的艺术话语和艺术现场。
80年代后期,在艺术学院从事教学与创作的部分艺术家明确提出“纯化语言”,强调创作要回到艺术本体,将艺术形式和语言作为创作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艺术学院将“形式探索”视为自由创作的落脚点。在不同历史时期,围绕艺术语言问题,艺术家和理论家多次展开过激烈讨论。在此后的传播、演化中,“纯化语言”将艺术语言、技法、形式与内容、思想人为地分隔开,强调前者的优越性、本质性。这对后来创作中将观念与形式对立、理解和践行形式实践,具有深远影响。
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与规制,是新政权建构其意识形态的手段之一。艺术家在不同阶段都要面对意识形态的规训、筛选和扬抑。在这个过程中,“艺术本体”是一个避风港,可以借以争取创作上的自由。但是同时,它也带有一种惯性,即将艺术语言与艺术中的思想分离开来;在实践中,也可能演化为一种封闭的思考机制。
我们在展览中运用两个文献单元,呈现了40年代至今,部分艺术家和理论家围绕艺术问题的相关论述、出版和创作实践。这些例子,勾勒出长期以来艺术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及艺术家、理论家们在与主流价值的互动中的思想状态和轨迹。这可以视为一个持续的对艺术进行纯化的过程。

叶浅予,燕山小溪,1956,纸本设色,44 × 34 厘米,由杨继栋先生惠允
在“语言纯化”的两个音区中,第一个音区聚焦于40年代末期至60年代末,从叶浅予的一篇文章和一幅作品开始。在其作于1949年末、1950年初发表在《人民美术》上的《从漫画到国画(自我批判)》一文中,叶浅予先提出了新建政权之下艺术家在创作思想上面临的若干问题、困惑并联系到自己的经验和态度谈及“现实”。对现实的重新理解、丑与美的判定标准、形式主义的倾向等多方面理论问题的探讨实际上是在不断试探着去调试自己的思想,以期使其适合时代的发展和要求。所谓检讨和新观点的阐明又好似在立下决心改造自己的艺术。创作于1956年的国画《燕山小溪》是艺术家将这种思考转化为创作实践的首度尝试。在这幅作品中,叶浅予从自己熟悉的漫画创作领域转向了以国画作为媒介,写生北京燕山的一处小景。展柜中呈现的《叶浅予绘画小品》一书即作为他的“改造成果”被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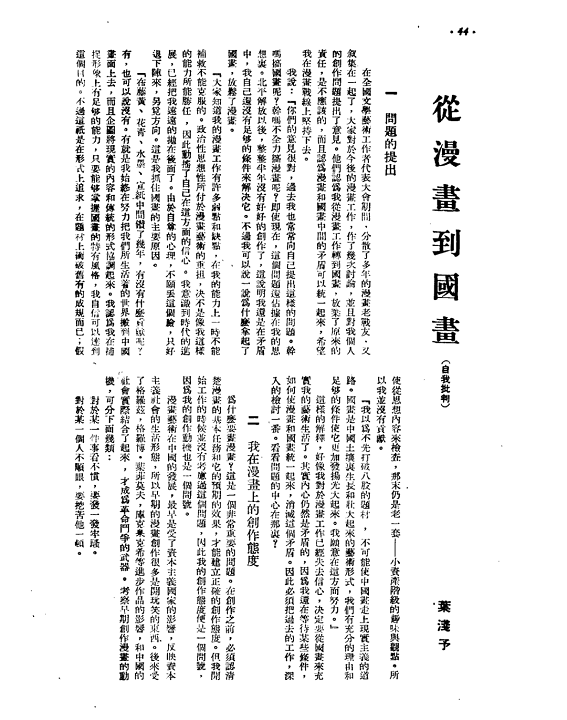
叶浅予,《从漫画到国画(自我批判)》,《人民美术》,1950年第1期

章节“语言纯化的两个音区”中的叶浅予作品及文章
1949年之后,政治上的阶级理论逐渐浸入文化批判与思考当中,在一些情形下甚至成为了其前设。1956至1958年,在中国、苏联,以及东德、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人民民主国家”,西方一些国家(如法国)的左翼文学界中,发生了具有“世界性”规模的现实主义辩论,主题是如何看待、评价已经有20年(或更长时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洪子诚教授在《1950年代的现实主义“大辩论”——以两部论文资料集为中心》一文中对于促发这场辩论的世界性背景,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概述:“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部分西方左翼文学界来说,30年代在苏联确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学观念、创作方法,而且具有思想原则的‘纲领性’意义。在斯大林—日丹诺夫时代后期,它的理论阐释和实践加剧了机械论、庸俗社会学的份量,质疑之声和不同意见的交锋也不断浮现。随着斯大林死后苏联政治变革和权力转移,对这一“文艺纲领”的反思提上日程也就不感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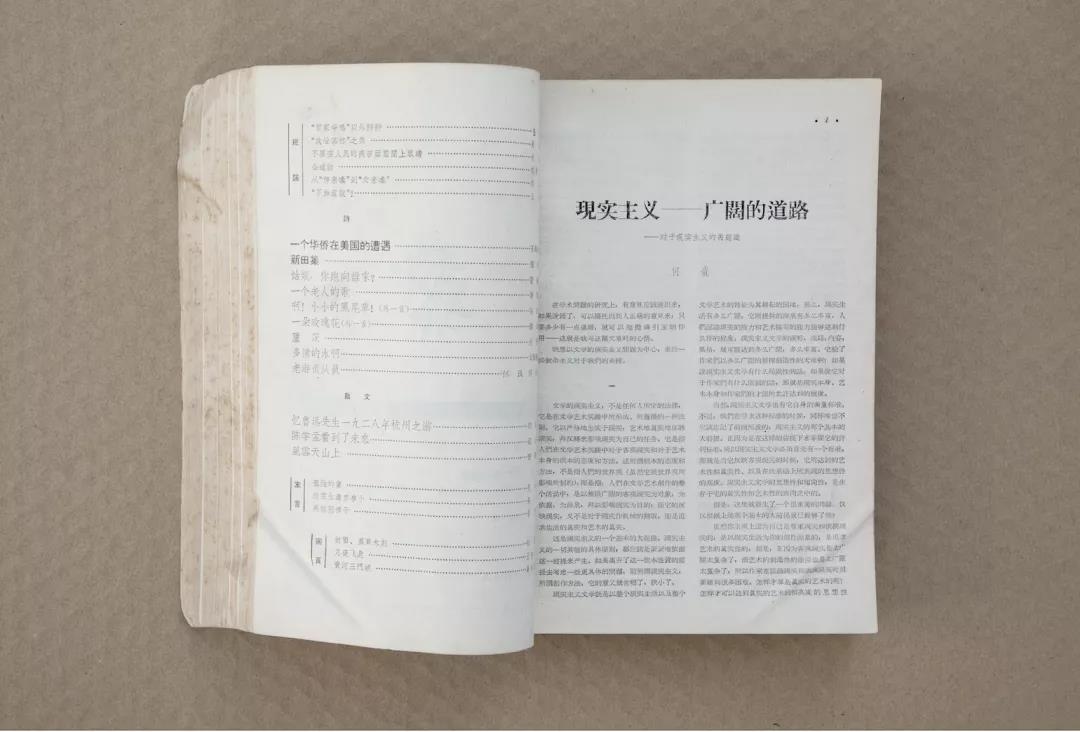
秦兆阳(何直),《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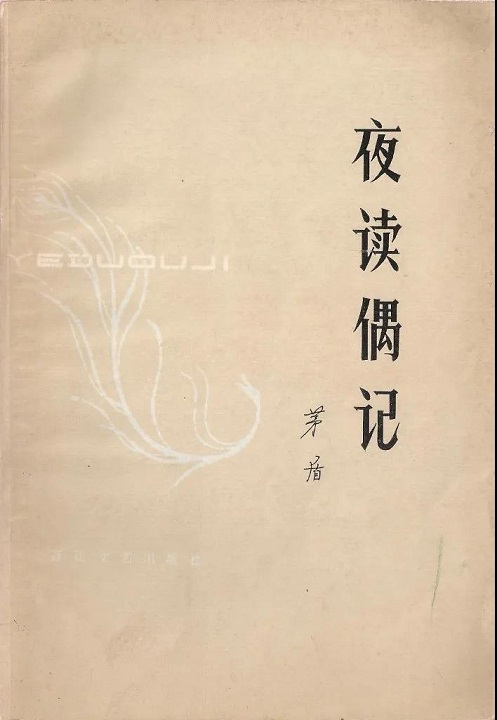
茅盾,《夜读偶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一版
在中国,1956年,作家秦兆阳(署名“何直”)在《人民文学》第9期上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引发热议。这篇文章的副标题“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缘于作者对文学现实的忧虑。秦兆阳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负责这份刊物的编务。这是他作为中国权威文学杂志负责人的见证描述。此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在收入国内材料时全部呈现的是“一面之词”,质疑、批评机械论和文学现状问题的文章,大多被屏蔽。秦兆阳写作这篇文章时,是出于对社会主义文学的拳拳之心,为出现的弊端心焦。可是作者却因它成了右派。在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讨论之下,拥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大部分人的选择。茅盾的《夜读偶记》呼应着此番讨论,阶级立场自然明确。该书历来被认为是当代文学讨论现代主义的重要文献。不过,此种既成判断实际上遮蔽着该书付梓的1958年左右复杂的时代语境和思想界动态。
我们将这一思想线索平行地转移到同时期的艺术界的探讨中,聚焦于“印象主义”的争辩。一方面,江丰著文旗帜鲜明地指出“印象主义不是现实主义”;另一方面,林风眠仍在教授、引介印象派的经验。看似是风格、语言的讨论、分歧背后潜藏着意识形态的迥异取向。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制造出热烈异常的话语景观。《美术》杂志编辑何溶就曾以山水、花鸟画切入连续写下三篇议论。所谓“牡丹也好,丁香也好”就是对百花齐放原则的运用和强调。何溶反对“题材决定论”,对艺术本体的强调成为他争取创作自由的撬点:“文学艺术虽然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可是它和政治终究不是完全相同的。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直接表现形式,文学艺术可以直接地表现阶级斗争,也可以比较曲折地表现阶级斗争。至于曲折地表现阶级斗争到底曲折到什么程度,尤其在美术这个领域之内,是个复杂的问题。”尽管这些讨论落脚于艺术风格和形式的问题,但其实质是为自由创作争取空间的一种呐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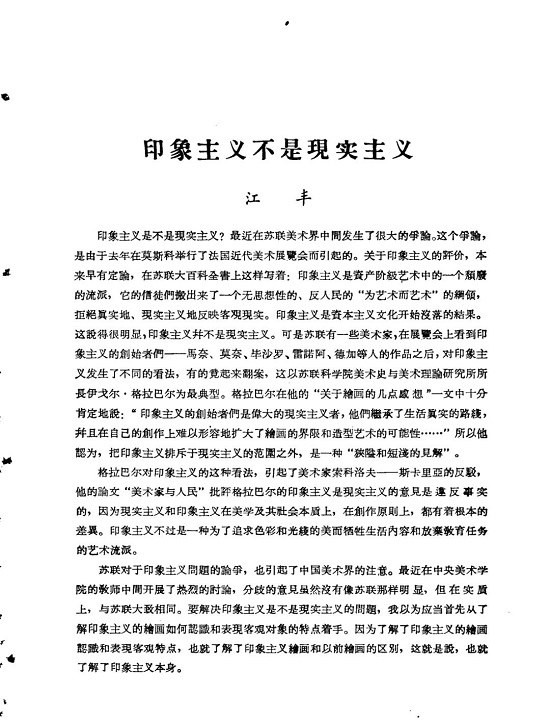
江丰,《印象派不是现实主义》,《美术研究》,1957年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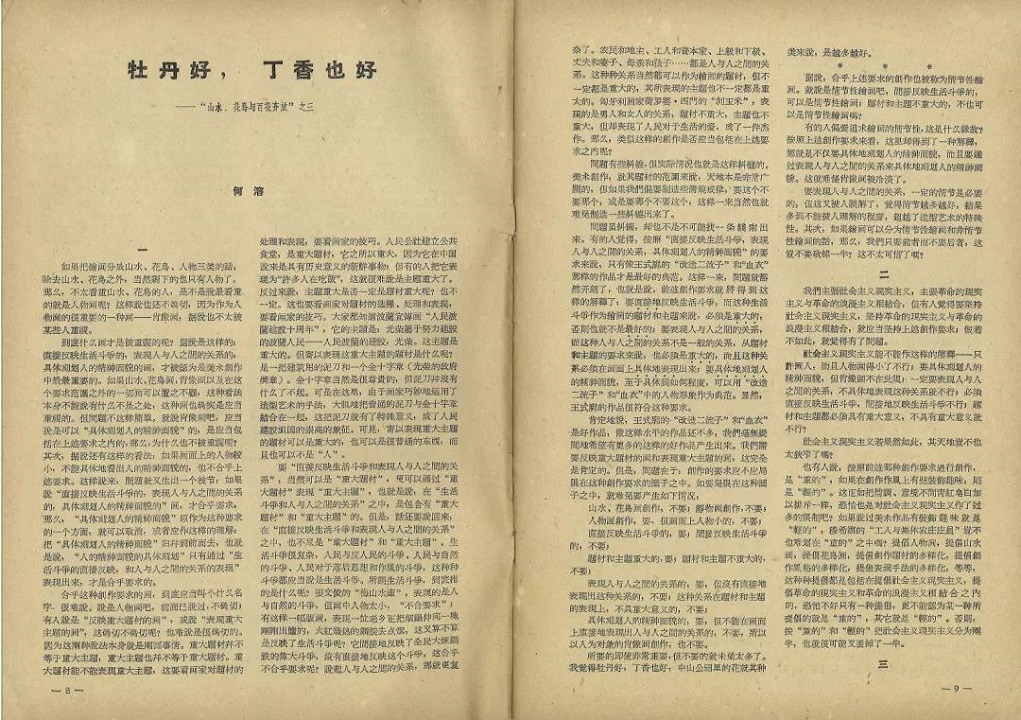
何溶,《牡丹好、丁香也好-山水、花鸟与百花齐放之三》,《美术》,1959年第七期
(注:何溶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直至1981年,他又在《美术》上发表《再论牡丹好,丁香也好》一文,论述“反题材决定论”这一观点,主张艺术创作的个性化和艺术方法的多元化,提倡反映对代精神和民族精神。)
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席卷而来,何溶那种基于艺术本体的纯化必然受到批判。而二十余载以来的争论最终走向以政治“纯化”艺术的高潮,在此“纯化”中,艺术被剥夺了它的主体位置,让位给政治忠诚及信条。作为“文化革命旗手”的江青本就是文艺战线的老工作者,她在文艺界会议上、文艺座谈会上屡屡发言被集结成书,这些话语也最终亦溢出了单纯的艺术问题讨论,将“纯化”的力量推向政治化的高潮。
撰文:张理耕
编辑排版:孙杲睿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