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实践 Yishu写作者修行之路 系列采访 #11
展览“从艺术到Yishu,从Yishu到艺术”(2020.12.19-2021.05.09)已顺利闭幕。在此,我们特别感谢郑胜天、林荫庭、华睿思、白慧怡、田珠莉、康书雅、姚善嘉、林似竹、史楷迪、帕特里夏·艾肯鲍姆·克雷斯基、于渺、乔安妮·伯妮·丹妮克、杜伯贞、顾珠妮、杨天娜、斐丹娜、林白丽、刘千、刁雪、倪嘉、陈佳树、祝天怡、韦淇、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对于本项目的支持与帮助。
在今后的两个月里,我们仍将继续发布 《Yishu国际典藏版》写作者和编辑的中英文访谈。他们中既有资深的双年展策展人,也有艺术史家和活跃的评论家。我们希望从他们的写作修行之路中汲取灵感和能量,并从中看到艺术出版的生态,以及《Yishu》作为其中一个可贵的案例。

杜柏贞
杜柏贞,现任亚洲艺术文献库(香港及纽约)董事会主席。1996年,杜氏作为展览“中国五千年”(China: 5000 Years)的项目总监加入古根汉美术馆,该展览在1998年先后在纽约及西班牙毕尔包的古根汉美术馆展出,是一个中国传统及现代美术的大型展览。此后,她出任古根汉美术馆的副馆长,负责美术馆的全球运作及展览事务,直到2002年移居香港为止。杜氏从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及香港大学获得艺术史硕士及博士学位,她的近作《国家与市场之间: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当代艺术》于2014年由博睿学术出版社发行。
1. 你和《Yishu》的故事是什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为《Yishu》写作的?
2002年,我曾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学、老同事朱莉娅·安德鲁斯(Julia (Judy) Andrews)首次向我介绍了《Yishu》,她从《Yishu》创刊以来一直担任该杂志的编委。她对创办一本专注于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英文刊物十分感兴趣。我也一样,因为有关这个庞大而复杂的主题,在英文平台上的介绍少之又少。令我印象深刻的是,《Yishu》拥有双重潜力:它不仅能提高人们对在中国正在翻天覆发展的艺术的认识,而且还能为成熟和新兴的批评家、策展人、艺术史学家和艺术家提供机会,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批评写作技巧。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需要有智慧的、非市场驱动的关于中国艺术的讨论和辩析的渠道。
2. 你在《Yishu》中发表过几篇文章?主要写作的内容是什么?
我是一个读者,并非一个写作者。更多时候,我把自己当作一个爱好者,而不是专家。因此,每当看到自己的文字刊载在刊物上,尤其是与更有见识的同仁的文章刊登在一起,我总是感到有些惊讶。我很荣幸我的文字曾两次被《Yishu》刊登:一次是在2005年,还有一次是在2020年的纪念刊上。作为古根海姆博物馆亚洲艺术委员会组织的一次圆桌讨论的主持人,我的观点也发表在2015年的《Yishu》上。
回顾2005年我发表在《Yishu》上的文章,我发现情况既有变化也有不变。《中国当代艺术:在美国主流的边缘》,这篇文章改编自我在当年1月由林似竹(Britta Erickson)和理查德·维诺格拉德(Rick Vinograd)组织的会议上的一篇论文,这个会议是为了配合斯坦福大学坎特视觉艺术中心的 “边缘:当代中国艺术家与西方的邂逅 “展览的开幕。这个展览在美国不同地方巡回展出,还附有一本内容丰富的画册。
自从写了那篇文章之后,艺术市场飞速发展,画廊和艺术博览会大量涌现。同样,在中国国内建立了许多致力于当代艺术的博物馆,它们中的一些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虽然这些变化已经发生,但我感觉在美国,那些经验丰富的学者和有才华的策展人即便做了很认真、有价值的尝试,中国艺术仍然处于美国主流艺术的边缘。在有资历的艺术杂志中,比如《ARTNews》、《Art in America》和《Artforum》——刊登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文章并不多见。如果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于2019年重新开放的展览为例,大型现代艺术博物馆对中国艺术的收藏依然稀少。
3. 你为什么会选择《Yishu》平台?你觉得《Yishu》杂志的特点是什么?它有哪些特质是不同于其他杂志的?
《Yishu》恰好填补了一个空白。作为一个由中国艺术专家组成编辑部的出版平台,《Yishu》用英文提供了业内人士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看法——这是非常必要的。虽然主流杂志上的常规报道和新闻报道也发挥着他们的作用——它们可以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也更广为流传。但在《Yishu》中关于中国的文章则更具特殊性,它们向大家提供了一种罕见的深度和关注重点。我们需要更多的《Yishu》。
4. 跟《Yishu》杂志编辑部合作沟通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我与《Yishu》编辑们的合作一直很专业,而且也很顺利。
5. 借用华睿思在第一百期向写作者进行的提问:“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当代艺术在艺术生产和运作机制方面有些什么发展/变化?”,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
我曾为《Yishu》2020年纪念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 《合作当代》——内容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这20多年来,人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普遍态度发生了变化——至少从我在纽约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因为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我一直待在纽约,从未离开,许多观察者由原本充满热情,到现在变得怀疑,甚至心灰意冷——人们对全球艺术界的感受不也是一样的吗?特别在商业艺术过于繁荣的现状下,大型画廊占据主导地位,注意力大多集中在那40位相同的艺术家身上。这种情绪的转变,对《Yishu》和这个领域意味着什么?就我而言,这种态度的转变意味着: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像《Yishu》这样持续讨论和对话的平台。这是确保深入的学术研究和细致的、基于知识的评论继续下去的唯一途径。唯有如此,无论是2000年代初的夸夸其谈,还是今天的失望沮丧,都不会妨碍我们对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现实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和敏锐的判断。
采访策划:刘语丝,黄文珑
采访翻译:刘千
文字校对:倪嘉,张理耕,黄文珑
微信排版:刘千
展览视觉设计:On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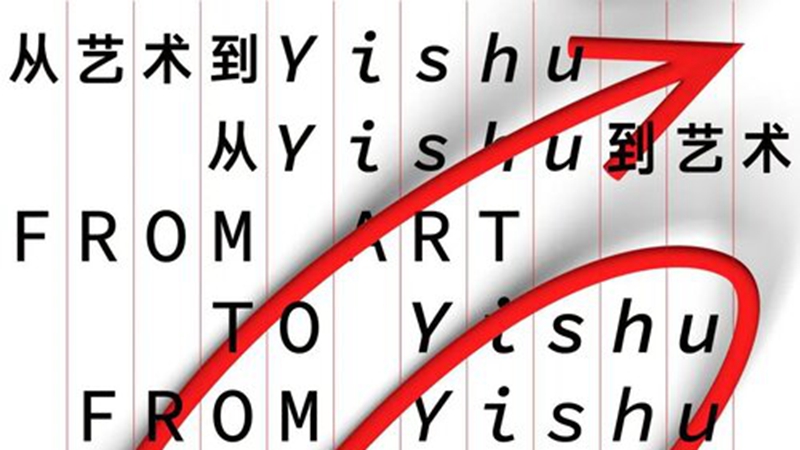
发表回复